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 1866–1924)是二十世紀初最具影響力的義大利鋼琴家/作曲家之一,以驚人的鋼琴技巧、前衛的音樂思想與經典改編著稱:從 Bach–Busoni〈夏康〉,到結構龐大的《C 大調鋼琴協奏曲》Op.39,以及以《卡門》素材重構的《室內幻想曲》(Sonatina No.6, BV 284)。本文一次掌握布索尼的生平、風格、三大鋼琴名作。
布索尼 生平
概覽
- 1866/4/1:生於義大利托斯卡尼・恩波里(Empoli)。父 Ferdinando 為單簧管演奏家,母 Anna Weiss 為鋼琴家;童年多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成長。
- 1870s–1880s:以神童之姿活躍歐陸;陸續作曲、演奏並出版早期作品。
- 1894:遷居柏林,此後長期在此教學、創作與演出。
- 1901–1904:完成《C 大調鋼琴協奏曲》Op.39(1906 出版;1904 柏林首演)。
- 1907:發表《新音樂美學綱要》(Sketch of a New Aesthetic of Music),倡議突破調性與形式框架,影響深遠。
- 1920–1921:完成並出版《室內幻想曲:取材自〈卡門〉》(Sonatina No.6, BV 284)。
- 1924/7/27:於柏林逝世,享年 58。
早期生活(1866-1886)
布梭尼於1866年4月1日出生於托斯卡尼地區的恩波利(Empoli),一個音樂家庭之中。他的父親費迪南多(Ferdinando)是一位傑出的單簧管演奏家,母親安娜・懷斯(Anna Weiss)則是一位才華橫溢的鋼琴家家。這獨特的家庭背景,從生命之初便為他注入了義大利與德國的雙重音樂基因:父親代表了義大利的器樂炫技傳統,而擁有德國血統的母親則為他奠定了德奧音樂的基礎。
布梭尼的童年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度過,由母親親自啟蒙鋼琴 。他驚人的天賦迅速展現,七歲時便與父母一同公開演出 。1875年,年僅九歲的布梭尼被父親帶往維也納,進入著名的音樂學院學習。但僵化的學院體制卻令他感到窒息 。這次經歷促使家庭遷往格拉茨(Graz),從1878年到1881年,布索尼師從威廉・邁爾(Wilhelm Mayer,筆名W.A. Remy)學習作曲。邁爾不僅向他傳授了嚴謹的對位與和聲技巧,也引導他深入研究巴赫(J.S. Bach)與莫札特(W.A. Mozart)的經典,為日後的美學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基石 。在此期間,他也已是一位活躍的少年演奏家,其才華甚至得到了當時權威樂評家愛德華・漢斯立克(Eduard Hanslick)的認可。
遊學歲月(1886-1894)
二十歲時,布梭尼做出了其藝術生涯的第一個關鍵決定:前往萊比錫。此舉不僅是為了進入當時歐洲最活躍的音樂中心之一,更是為了「擺脫父親藝術監護的沉重之手」,尋求個人的智識獨立與藝術解放 。萊比錫時期是他建立人脈、擴展視野的關鍵階段。在這裡,他結識了葛利格(Edvard Grieg)、戴流士(Frederick Delius)、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及馬勒(Gustav Mahler)等樂壇巨擘,並與小提琴家亨利・佩特里(Henri Petri)一家結下深厚友誼,其子艾貢・佩特里(Egon Petri)後來成為布梭尼最親密的學生與摯友。
此後,他的足跡遍佈歐洲。1888年,他受聘於赫爾辛基音樂學院擔任鋼琴教授,期間與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成為好友,並邂逅了未來的妻子,瑞典雕塑家之女潔達・蕭斯特蘭(Gerda Sjöstrand)。1890年,在安東・魯賓斯坦(Anton Rubinstein)的引薦下,他轉往莫斯科音樂學院任教,並以其《為鋼琴與管弦樂團的協奏曲小品》(Konzertstück, Op. 31a)贏得了著名的魯賓斯坦作曲大賽首獎 。1891年,他橫渡大西洋,前往美國波士頓的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執教。雖然教學工作為他帶來了穩定的收入,但布梭尼很快便意識到自己的天職在於演奏與創作。在長子班維努托(Benvenuto)出生後,他辭去教職,移居紐約,全身心投入到音樂會演出中。
柏林時代(1894-1915)
1894年,布梭尼返回歐洲,選擇柏林作為他永久的定居地。柏林對他而言,成為了「進行智識工作與作曲創作不可替代的優越之地」。在這裡,他達到了個人事業的巔峰,其身份也擴展至指揮家、教育家與知識界的領袖。他曾執掌柏林愛樂樂團,並在節目中積極推廣荀白克(Arnold Schoenberg)、巴爾托克(Béla Bartók)等當代作曲家的作品。
這是布梭尼創作力最為旺盛的時期,完成了被自己視為「真正第一部作品」的《第二號小提琴與鋼琴奏鳴曲》(1900);創作了結構宏偉、思想深邃的《C大調鋼琴協奏曲》(1904),作品編號39 ;發表了標誌其風格重要轉捩點的鋼琴《悲歌集》(Elegien, 1907);並基於巴哈未完成的賦格創作了不朽的《對位幻想曲》(Fantasia Contrappuntistica, 1910)。更重要的是,他在1907年發表了其音樂哲學的代表性文件——《新音樂美學概論》,系統地闡述了他對音樂未來的革命性思考。
流亡與內省(1915-1920)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再次打亂了布梭尼的生活。他於1915年初前往美國進行了一系列凱旋般的巡演,但歐洲的戰火與日益緊張的政治氛圍,使他深感自己無論在義大利還是德國都處於尷尬的境地 。同年秋天,他選擇向中立國瑞士尋求政治庇護,定居蘇黎世。
在蘇黎世的五年流亡生涯,儘管在心理上是艱難的,卻意外地成為一段藝術上極為豐碩的沉潛時期。遠離了繁忙的音樂會舞台,布梭尼得以將精力集中於最為宏大和個人化的創作項目上。在此期間,他完成了浩瀚的巴哈-布梭尼鋼琴改編版全集的編輯工作,創作了歌劇《阿萊基諾》(Arlecchino)與《杜蘭朵》(Turandot)(均於1917年首演,跟普契尼的杜蘭朵不一樣喔),並為其畢生鉅作《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譜寫了大部分樂章 。正是在這段被迫的靜思中,他開始系統地闡述其「青年古典精神」(Junge Klassizität)的理念。他在蘇黎世的家,也成為了當時流亡藝術家們的聚集地。
柏林晚年(1920-1924)
1920年9月,布梭尼回到了戰後的柏林,並被任命為普魯士藝術學院的作曲教授 。他將生命的最後精力投入到教學中,培養了包括庫爾特・懷爾(Kurt Weill)在內的一批傑出學生 。然而,戰後的惡性通貨膨脹幾乎耗盡了他多年積累的財富,加之健康狀況日益惡化,迫使他不得不與時間賽跑,以完成他視為生命終極目標的歌劇《浮士德博士》。
1922年5月,他舉行了最後一場公開鋼琴獨奏會,此後便告別了舞台 。他將所有心力都傾注在《浮士德博士》的創作上,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1924年7月27日,在柏林逝世,享年58歲,遺憾地未能完成這部鉅作的最後一幕 。他最忠誠的學生菲利普・亞爾納赫(Philipp Jarnach)根據其草稿補完了全劇,並於1925年在德勒斯登舉行了首演。
布索尼的音樂風格
演奏
演奏風格,可以用鋼琴家阿爾弗雷德・布倫德爾(Alfred Brendel)的精闢評價來概括:「它標誌著沉思對炫技的勝利」。在李斯特所開創的華麗 flamboyant 演奏風格之後,布索尼引領了一種更為內省、更具分析性的演奏路徑。他鄙視將技巧本身作為目的的演奏方式,儘管他本人擁有爐火純青的技術。他的演奏方式是理性的、具有高度分析性的,他會對樂譜進行深入的智力剖析,探求其內在的結構與邏輯。
他曾言:「音樂的構成如此,以至於每個語境都是一個新的語境,應被視為一個『例外』。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案,一旦找到,就不能被重新應用於不同的語境中。」他反對任何僵化、一成不變的詮釋範式。每一次演奏都是一次獨特的、基於當下情境的再創造。他大膽地進行樂器實驗,特別是在踏板的使用上,以求創造出前所未有的音色效果與共鳴層次。
音樂哲學:《新美學》與《青年古典精神》
布梭尼的音樂哲學主要體現在兩個核心概念中:其一是在1907年出版的《新音樂美學概論》(Sketch of a New Esthetic of Music)中提出的革命性思想,其二是在其晚年逐漸成形的「青年古典精神」(Junge Klassizität)理念。
《新音樂美學概論》充滿先知灼見,在書中,布梭尼提出了一系列顛覆性的觀點。他認為音樂是一門「尚未完全實現其潛能的年輕藝術」。他呼籲將音樂從一切傳統形式、規則、甚至包括十二平均律體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他預見了微音音樂(microtonalism)的可能性,並提倡一種超越標題音樂具象描繪的「絕對音樂」,這種音樂應直接反映自然與情感的精髓,而非模仿其表象 。這本小冊子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爭議,但也極大地啟發了新一代的作曲家。
「青年古典精神」則是布索尼對如何處理傳統與創新關係的最終回答。這個概念絕非等同於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式的、回歸古典時期風格的「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布梭尼所設想的,是一種更為辯證的綜合。他將其定義為「對所有過往經驗成果的掌控、篩選與利用,並將其融入堅實而優美的形式之中」。這不是向後看的復古,而是向前看的融合。代表了一種音樂傳統的自然演進,堅決反對在音樂歷史中劃出「元年」、徹底割裂過去的激進做法 。其核心思想是:唯有在完全掌握過去的基礎上,才能充滿信心地開創未來。這是一種在不否定古人的前提下,尋求新事物的創作態度。

作品欣賞
Bach-Busoni: Chaconne in D Minor
他對巴哈鍵盤作品的改編與詮釋,算是他最集中、持久的創作之一。他的「巴哈-布梭尼」版本,不僅是學術性的校訂,更是一種藝術再創作。他堅信巴赫的音樂具有一種「普世性」,其內在的音樂「理念」是超越時代與樂器的 。因此,他的目標不是機械地將為管風琴或古鋼琴寫作的音樂移植到現代鋼琴上,而是要用現代演奏會大鋼琴的全部潛能,去揭開巴哈音樂中蘊含的宏偉精神。
他對巴哈《d小調無伴奏小提琴夏康舞曲》(Chaconne in D minor, BWV 1004)的鋼琴改編版,與其他改編者,如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形成了鮮明對比。布拉姆斯為左手寫作的改編版,力求忠實地模仿原作小提琴的織體與線條 。而布梭尼則反其道而行之,他將這部獨奏作品擴展為一首具有「宏偉管弦樂或管風琴」規模的音響史詩。似乎受到了音樂學家菲利普・史畢塔(Philipp Spitta)對原作描述的啟發,史畢塔曾寫道,在夏康舞曲的高潮處,「它聽起來像一架管風琴,有時甚至像一整個小提琴樂隊在演奏」。
巴哈原作聆聽:
Carmen Fantasie [Sonatina No. 6, BV 284]
是一部極具創新性的作品,為Busoni為數不多的“超現實主義”作品之一。該曲源自於喬治·比才(Georges Bizet)的歌劇《卡門》(Carmen),但它不僅僅是對該歌劇的編曲或變奏。相反,它以更深層次的方式重新塑造了比才的音樂,創造出了一種新的音樂表現。
他的六首鋼琴奏鳴曲,以《第六號奏鳴曲:根據比才〈卡門〉的室內幻想曲》(Sonatina No. 6: Kammer-Fantasie über Bizets “Carmen”, 1920)最為知名,它完全不同於一般炫技的歌劇幻想曲。布梭尼並未簡單地串聯旋律,而是借鑒了李斯特處理《唐璜》主題的模式,對《卡門》中的動機進行了精密的解構與重組 。這首作品充滿了機智與巧思,但在其看似輕鬆的表面之下,一個陰鬱的尾聲為全曲增添了意想不到的深度與複雜性,反映出在創作《浮士德博士》期間複雜的內心狀態。
Plano Canserto in C Major, Op. 39
全曲分為五個樂章,連續演奏,總長度超過70分鐘,像是一部音樂風格的百科全書,融合了布拉姆斯式的莊嚴、李斯特式的華彩、華格納式的和聲、蕭邦式的詩意與羅西尼式的狂歡。
這部協奏曲革命性之處,在於它徹底顛覆了鋼琴作為獨奏樂器的傳統角色。在這裡,鋼琴不再是十九世紀協奏曲中與樂團對抗的「英雄」,而更像是一個融入交響織體的「鋼琴義務部」(piano obbligato)。獨奏家常常是在「聆聽、評論、裝飾與夢想」,而管弦樂團則承載著作曲家最具預言性的靈感。
- 第一樂章(Prologo: Andante sostenuto)以其富有力量和表現力的主題為聽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 第二樂章(Pezzo giocoso)是快速的樂章,其活躍的節奏和明亮的調性讓人想起了古典的鋼琴協奏曲。
- 第三樂章(Pezzo serioso)更為深沉,布滿了華麗的和聲與複雜的對位。
- 第四樂章(All’ Italiana: Tarantella)為作品增添了義大利風情,此樂章靈感來自南部的傳統舞曲Tarantella。
- 第五樂章(Cantico)是一首長篇的宗教讚美詩,為合唱與管弦樂團所演唱,這是鋼琴協奏曲中相當少見的實驗性結構。
作品的終曲更是一個驚人之舉:加入了一段由隱藏的男聲合唱團演唱的讚美詩,歌詞取自丹麥詩人亞當・歐倫施萊厄(Adam Oehlenschläger)的戲劇《阿拉丁》(Aladdin)。他的意圖並非將協奏曲變為神劇,而是將人聲作為一種新的音色,為樂團增添一個神秘、超驗的音栓層次,將整部作品引向一個形而上的昇華境界 。這部協奏曲,正是布梭尼對傳統協奏曲體裁的一次哲學性批判與重構。
Doktor Faust, 1916-24
《浮士德博士》是他的畢生心血的鉅作,與古諾(Charles Gounod)或白遼士(Hector Berlioz)的同名歌劇不同,他的劇本並非改編自歌德的文學經典,而是源於更古老的十六世紀德國傀儡戲 。這一選擇至關重要,因為傀儡戲鬆散、插曲式的結構,使他得以擺脫傳統敘事歌劇的束縛。
這部歌劇的戲劇結構是獨一無二的。摒棄了傳統的線性情節與戲劇衝突,代之以一種「主觀的、開放的形式」, favoring 「意識流」的展現,是一部哲學戲劇,探討的是天才、野心與救贖等永恆主題,而非一部通俗情節劇。
音樂語言同樣具有開創性。整部歌劇的音樂素材,幾乎完全由布梭尼先前創作的24首獨立的「衛星」作品(包括管弦樂、室內樂及鋼琴曲)建構而成 。這並非傳統的「集成曲」(pastiche)手法,而是對其的徹底顛覆。布梭尼以此證明他的信念:「音樂,無論在何處以何種形式出現,歸根結底仍然是音樂,僅此而已。」結構思維預示了史特拉汶斯基與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的某些特徵,是一部思想深度與音樂複雜度都達到頂峰的現代主義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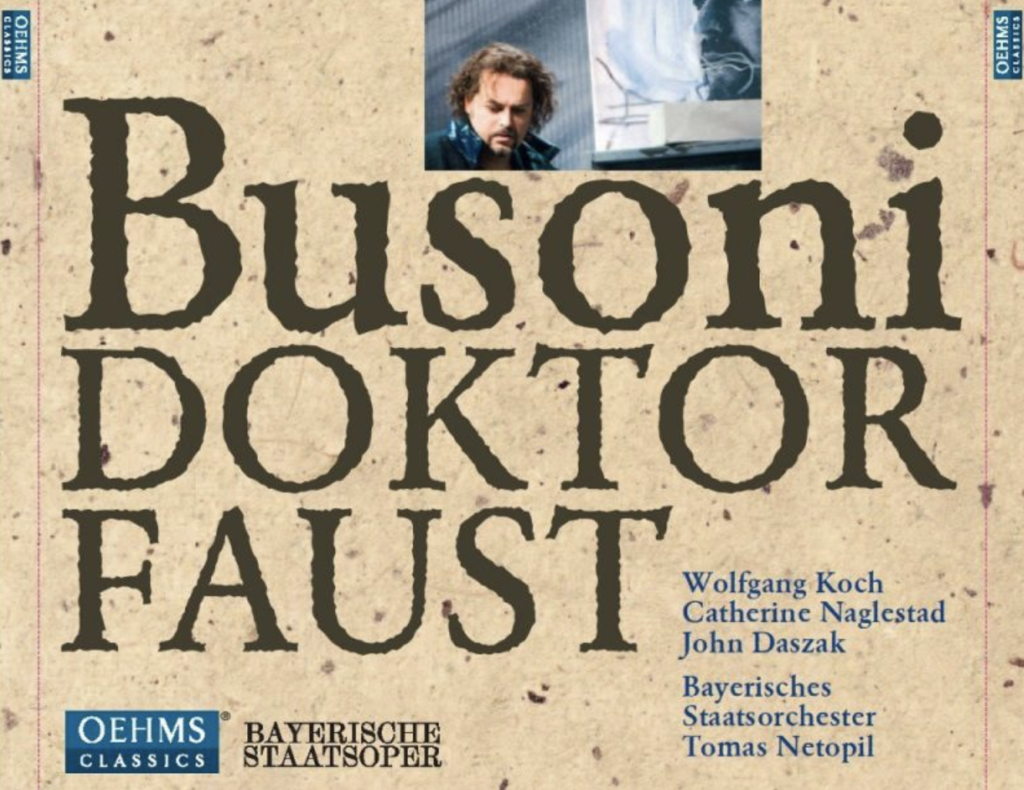
Fantasia Contrappuntistica, BV 256
這部作品是「青年古典精神」最純粹、最集中的體現。它的核心是為巴哈《賦格的藝術》(The Art of Fugue)中最後一首未完成的對位曲,譜寫一個宏偉的續篇。這不僅是一次學術性的補完,更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將巴哈的賦格主題作為基石,在其上建造了一座融合了現代複音技法、擴展和聲以及李斯特式鋼琴寫作的宏偉建築。
《對位幻想曲》雄辯地證明了他的信念:傳統並非靜態的遺產,而是一個活的、可以不斷演進的有機體。
RosyArts|古典音樂系列
想認識更多古典音樂?點這裡 ➜ 探索更多古典音樂


